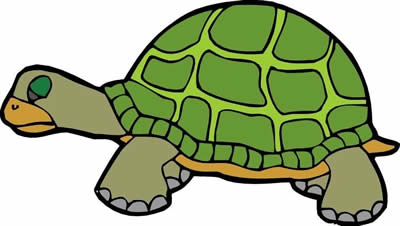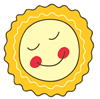一
我們——三名獸語大學的學生,勇氣百倍,而提心吊膽地向著大森林出發了。
和別的大學一樣,這最后一個學期安排學生實習,準備畢業論文。一般來說,學獸語的都去動物園實習,從籠子外面跟動物交談,既方便又安全。但我和我的伙伴認為,要想以后成為出色的動物工作者,必須精確、透徹地研究動物語言,而動物進了動物園后,語言可就不那么“正宗”了。我是學虎語的,我不愿意去找動物園里的老虎,因為虎籠的兩邊是豹籠和獅籠,它們互相影響,以至于那虎一張口就滿帶著獅音豹腔。并且,動物園里的動物囿于見聞,詞匯很貧乏,特別是那些在動物園出生的動物,問它們:“森林”、“清泉”、“野花”怎么發音?算是白問。它們甚至連蘑菇都不知道。它們的常用語幾乎只剩下了兩種,一種是抱怨游客又把桔子皮、蘋果核扔進來了,一種是催促飼養員快來喂食。
我們要去和野生動物接觸。我們下定了決心,做好了準備。除了個人必需品外,我背了一個太陽灶;“狼兄”(我們這樣稱呼這位學狼語的同學)帶了一大堆罐頭;“野豬兄”(自然是學野豬語的)則扛了一桿槍,可以射出麻醉彈。不能不考慮到特殊情況下的自衛,野豬兄是同學中的神槍手,所以我們很放心地把性命托付給他。
前面就是森林。我們開始注意泥地上的各種腳印,盼望能盡早找到各自的對象。正在這時,林中竄出幾只野獸。
“不是狼。”狼兄判斷道。
野豬兄也搖搖頭,“不會有這樣大的野豬。”
“是老虎!”我可高興了,“三只老虎!”
三只老虎看見我們,互相嘀咕了幾句,其中個頭較大的一只向伙伴吼了一聲。
“它說什么,虎兄?”兩位同學趕緊向我請教。
我為這么快就用上自己的專業知識而得意,“嗯,它是說,‘抓住他們!’”
“那,快跑吧!”
“別慌,”我說,“讓我上前交涉。”
可這時老虎們已經撲了過來。
我有把握通過我的解釋消除對方的敵意,但我沒來得及,在我身后響起了槍聲。野豬兄這家伙沉不住氣了。他這一開槍,狼兄也跟著像扔手雷一樣扔起罐頭來。
“砰!砰!砰!咚!咚!咚!”
突然我覺得渾身一震,我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事兒。我正要回頭責怪我們的神槍手,怎么慌里慌張把子彈打進我的身體?但這時已是四肢發麻,眼前模糊,我就這樣極冤枉、極不應該地倒下,并失去了知覺。
二
我醒來時,伙伴們早已不知去向。我恨恨地從屁股上拔出麻醉彈的彈頭。
老虎們看來都沒中彈。它們正快快活括地忙碌著。它們將樹一棵一棵拔起來,又一棵一棵栽到我的周圍
“你們在干什么?”我用虎語向離我最近的那只老虎發問。
那只老虎覺得驚奇:“你也是只老虎嗎?可你的樣子和我們不大一樣。”
我告訴他,不會有像我這樣子的老虎的,我只是個比較聰明的人,因為比較聰明,所以我說老虎的話。解釋完了,我又提出剛才的問題:“你們在干什么?”
“這個,你得去問咱們的大哥瑪烏。”它指了指那只個頭較大的老虎,“它叫咱們這樣干的。只有它走出過森林,所以只有它才會想出這樣的新鮮主意。”
“哦,瑪烏,”我說,“如果你們是在為我蓋房子的話,我很感謝。可是房子并不是這樣蓋法的呀。”
瑪烏一邊繼續干它的,一邊回答說:“可我知道房子是這樣的,至少有一種房子是這樣的。”
“你在哪兒見到這種房子的?”我問。
“在人的森林里。”我覺得這個用語很有意思,連忙記入我的筆記。“你們把我們的兄弟關起來,還關了許多豹啊,熊啊,獅子啊,就用這種房子。”
“那是動物園!”
“對,就是這個說法。我到那兒去的時候是夜晚。我不明白你們為什么要把人家抓來關在這里。里面的兄弟告訴我:‘關起來讓大家看唄。’我本來想救它們出來,可沒能成功。我臨走時,它們再三囑咐我,一定也要在森林里造一個動物園,抓幾個人關在里面,讓森林里的伙伴來看他們,向他們扔東西。”
我這才恍然大悟!
我本來就準備在森林里生活一段時期,為我的畢業論文積累材料,住哪兒都無所謂的,但我怎么也沒想到會被安排在動物園里,這可太有損人的尊嚴啦。
“不,我不住這兒。”我說,“要我住這兒的話,這兒不能叫‘動物園’,因為我不是動物呀。”
可是瑪烏說:“既然你們可以把我們當動物,我們也可以把你們當動物,這很公平。”
如果你遇上一個執拗的人,你會覺得很難對付。如果你遇上的是一只執拗的老虎,那可就毫無辦法啦。
我只好讓步。不管怎么說,人還算是高級動物嘛。
既然承認這是動物園,我就按照動物園的要求提意見了:“瞧,你們的柵欄太稀疏了,應該更緊密一些。這些樹干拼成的柵欄,可以容我側身鉆出,而一般來說是不該讓園內的動物有逃跑的機會的。”
可是瑪烏說:“要讓人家來看你,總得給人家看清楚。柵欄太密了,把動物整個兒都擋住了,那還看什么?”
這話有道理。我必須立即做好被展出的精神準備。但我首先需要的是物質準備----我肚子餓了。
我馬上大叫:“拿東西來吃!你們要給動物吃東西的呀!”
三只老虎慌了,不知怎么辦才好。
我讓老虎們把狼兄用來和它們作戰的那些罐頭撿回來。它們立即答應照辦。
不一會兒工夫,各種各樣的罐頭在柵欄前堆成花花綠綠的一堆。【m.pthirty1.com 兒童睡前故事】 老虎們恭恭敬敬蹲在一旁,等著看我進餐。大概他們想,這個人竟能用這些鐵家伙當食物,實在很值得欽佩的。但也正在這時,我想起我沒帶著罐頭刀,這東西也是由該詛咒的狼兄掌管的。我竟沒法打開這些罐頭了。
“喂,為什么不吃?”瑪烏問我。
我為難地說:“是因為缺乏某種合適的工具。”
“我們能幫一點忙嗎?”
我注意到老虎的銳利的尖牙。我便教瑪烏,先用尖牙扎穿鐵皮,然后順勢劃出一個半圓,這樣就能將盒蓋掀起了。瑪烏做得很認真,很起勁。
當我心滿意足地將那個罐頭享用完畢,我發現:老虎們已將所有的罐頭全部打開!
如果我有老虎那樣的胃口,這點罐頭自然不在話下。可現在弄得我啼笑皆非,不知所措。
“你吃不下嗎?”瑪烏替我發愁,“我們仍然可以幫你的忙。”
我想打開了的罐頭容易變質,我甚至不能把它們留到明天,萬一吃出病來,這里又沒有醫生。在已經無法自私的情況下,我的慷慨的本性便顯露出來。
“請嘗嘗吧,諸位。不過你們要知道,在一般動物園里,動物請飼養員吃東西的事是很少發生的。”
三
我把罐頭全請了客。這樣,我剛開始我的森林生活,就耗盡了帶來的所有食物。
動物園造好后,三只老虎要請大家來參觀。
我問:“準備請誰?”
“不管是誰,都請。”
“也請兔子、羚羊它們嗎?”
“當然。”
“它們肯來?不怕被你們吃掉?”我感到奇怪。
老虎們也感到奇怪,“請它們來看動物,怎么會干這種事情?就是獅子、豹子,也不會趁這種機會找食吃,這不像話呀。”
看來在這里大家認為只有公開狩獵才是獲取食物的正當方式。
“但我認為這沒什么不像話。”我開導老虎們,“我們那兒的動物園是賣門票的。也就是說,不能白看。在那些兔子、羚羊來這兒參觀完了以后,可以把它們留作食物,這是它們應付的代價呀。”
我已經想象著兔肉和羊肉被烤熟后的香味……可是老虎們拒不同意。
這可真讓人失望。
瑪烏接著向我請教道:“聽說在你們那兒,你們是一邊扔東西一邊看動物的?”
這話問得我有些害怕,“嗯……有時候是這樣,不全是……而且扔的東西很小,不會打傷動物的。”
“那么,都是些什么東西?”瑪烏又問,“我們這兒石頭不多,用水果行不行?”
這可使我喜出望外,“行,行!就用水果,把寶貴的石頭留著吧。”
“照你剛才說的,是不是選一些小的水果,像葡萄、棗兒什么的?”
“不,大的也行,桃子,梨子,蘋果……越大越好!”
動物園正式展出了。以前我在籠子里看到過的各種野獸,如今在籠子外看我來了。
猴子向我扔香蕉。黑熊向我扔甜瓜。大象用鼻子把甘蔗撅成段兒扔進來。起初是扔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很快吃飽了,我便開始拾起水果朝外扔。我扔得很準,接二連三地命中目標。這一下“游客”們更興奮了。
一頭犀牛蹣跚地走來,向我瞪了幾眼,接著便抱怨地向老虎瑪烏訴說了一頓。
我不懂牛語。“它說什么?”我問瑪烏。
瑪烏翻譯道,“它說:‘這個動物一點也不好看,而且很笨,它有四條腿,但只有其中的兩條可以用來
我很不服氣,“我們當然也可以用四條腿走路的,只是我們不高興這樣走。”
“犀牛還說:‘既然犀牛最好看,’當然,這只是犀牛自己的看法,我就認為犀牛并不比老虎好看。它說,‘既然犀牛最好看,為什么不能把那家伙趕出來,讓犀牛住進去給大家好好看看呢?’”
我絕不承認自己不如犀牛。本來我對在動物園當動物不是很熱衷的,但這樣一來,我意識到被展出是一種榮耀,甚至可以說,是一種權利——一種已經屬于我的、但已被凱覦的權利。我絕不放棄榮耀,出讓權利。在這種情況下,從我身上表現出作為高級動物的某些特點。
那犀牛想闖進動物園,但對這些對我顯得過于稀疏的柵欄,對犀牛可就顯得過于緊密了。它終于沒能擠進來,我勝利了。
四
野獸們是很少有時間觀念的,但我很清楚地知道,我的頭發越來越長了,在這兒剩下的日子越來越少了。
我為我的畢業論文搜集到足夠的材料,記了滿滿一大本。
我即將結束這段有趣的經歷,令人驚嘆地回到親友身邊去。狼兄和野豬兄會為我的收獲難受得想自殺。
我對老虎瑪烏說:“我想,明天應該是我最后一次展出了。我雖然覺得自己并不難看,但你們總也看夠了吧?朋友,咱們該分別啦。”
瑪烏說:“你應該回到你的兄弟、伙伴那兒去,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兄弟、伙伴應該回到森林來。請你答應我,回去以后要說服管動物園的人,把關在里面的動物都放出來。你能答應嗎?”
我知道自己沒有說服別人的本領,要接受這樣的委托完全不自量力。當然,我可以隨便說一句:“行,我答應。”這并不費事,回去以后用不著真的去動物園交涉。但我在這兒住了不算太長也不算短的這么一段日子,天天呼吸著這種過于透明的空氣,飲用著過于純凈的泉水,森林居民的渾樸天真或多或少熏染了我,使我已不習慣面不改色地說謊,盡管是這樣一個不需要什么技巧的小謊。我感到很為難。
我說:“瑪烏,我沒法答應。”
“那么,”老虎被激怒了,“既然你們這么喜歡關人家,我們也可以這樣做!”
我嚇一跳,“你是說,我將一直被關在這里?”
“這樣做公平合理,不是嗎?”
“當然,當然……”我有些尷尬,但突然靈機一動,畢竟人的腦袋要管用得多,“我想了個好辦法!去給咱們市長送一封信,要求釋放關在動物園里的所有動物,就拿我當人質,保管成功!”
我向瑪烏解釋了什么是“人質”,瑪烏很高興,于是讓我代替它們起草一份致市長的通牒。
我在這通牒里模仿了恐怖分子的口氣。
市長大人閣下:
我們鄭重其事地通知您,您治下的一名獸語大學虎語系大學生,在我們妥善安排下,已經享受到你們給予我們同胞的同等待遇。我們希望與貴市動物園交換俘虜,即各自釋放動物園內的全部動物。限二十四小時考慮,否則……
我點上一長串兇險莫測的省略號。最后,由瑪烏帶頭,大家在這通牒下端按上各自的腳印、蹄印、爪印。
“派誰去送信呢?”我問瑪烏。
瑪烏把信折好,交給我,“你去吧。”
“我,我可是人質呀!”
“送過信,回來再當人質也不晚呀。”
這是信任,我可從未被人這樣信任過。
五
我揣著這封心甘情愿地抵押了自己的信,趕回城市——瑪烏所說的“人的森林”。空氣立刻渾濁得難以忍耐了。
去市政府的路上,我原想盡可能迅速地走過我家居住的那座樓房。可是突然有樣東西飄落到我頭上,我扯下一看,是我母親的圍裙。
我身負如此重任,當然不便面見家人。我想請一位行人代勞。
“喂,先生,瞧見了沒有——五樓從左數第三個陽臺……”
“瞧見了。”
“麻煩您把圍裙送上去。”
那人并不反問我自己為什么不送,而是一口答應,“行,給一塊錢吧。”
我覺得有些奇怪。這也許不該奇怪。去森林以前我大概也不會奇怪。我奇怪的神色反倒引起那行人的奇怪。
“嫌貴?爬一層樓只收兩角錢,這算是平價。”
“可買這圍裙才化了一塊五———”
“所以還值得嘛。上回七樓有位老病人掉了根拐杖下來,我給送上去,一層樓算他四角錢,那可是議價啦。再上回——”
我氣沖沖塞給他一塊錢,再不愿聽他羅嗦。
我趕到市政府,對傳達室的職員說,我有一封非常要緊的信,能不能立刻讓市長過目。
“那得先到信訪處登記一下。”那職員問我,“你這信反映的是哪方面內容?”
“呃,”我想了想.“應該是劫持,或綁架,一種值得同情的綁架。”
“好極了。我告訴你,信訪登記處具體分設若干個登記科,你找‘綁架事務登記科’吧”。
在“綁架事務登記科”,人家又問:“被綁架的是什么人?”
我回答:“一個大學生。”
“好極了。我告訴你,今天是星期三,專門登記綁架小學生的信件;中學生是星期五;星期一辦理專科生;下星期二你來吧,那時就輪到大學生了。”
我說,因為二十四小時內必須請市長采取行動,所以遞交信件刻不容緩。但我不再被理睬了。
人的語言不足以表達我的失望和感慨,我用虎語怒吼了一聲! 這時有人向我伸出手來,“把信給我吧,我保證讓市長今天就見到它。”原來這是
一位晚報記者,他是來找綁架新聞的。
我相信報紙的神通,便把信交給了記者。作為人質,我得立即返回森林。
六
我又回到森林。瑪烏它們見我竟然回來并不驚異,因為它們根本沒有懷疑過我。
當晚,我打開袖珍收音機,聽到關于我的廣播新聞——
據晚報快訊透露,一伙獸類恐怖分子綁架了一名大學生后,向本市市長發出恐嚇,要求釋放動物園內所有動物。為此,本臺記者特地訪問了市長先生。
記者:市長先生,請談談您對這事件的看法。
市長:不幸,很不幸。我希望沒被綁架的人不要對此產生好奇,那不值得嘗試,雖然我還沒嘗試過。總而言之,要提高警惕,加強戒備,防止類似的不幸事件再度發生。
記者:您對沒被綁架的人提出了誠懇的勸渝,這是有意義的。現在請您對已被綁架的人說幾句話,他可能帶了收音機。
市長:好的。被困在森林里的大學生,本市通過這溫暖的電波,向你表示慰問。關于用整園動物(包括許多珍稀動物)來交換一個普通學生,你知道,這不夠現實。交接只能在價值相當的情況下進行。且不算熊膽、貂皮之類的經濟賬,單以化去的勞動力相比,它們只抓了你一個,而我們抓了那么多個,很不容易呢。希望你能依靠人類的智慧自行脫險。再說你是學獸語的,完全有可能用偉大的人性去感化它們,從精神上壓倒它們.....
我不耐煩地關掉收音機,并將市長的高論譯給瑪烏它們聽。
瑪烏想了想,問我:“你知不知道市長家的地址?”
我說:“知道,離我家不遠,……”
當天夜里,瑪烏進城一趟,去把市長背了來。
市長被瑪烏的虎吼聲嚇得不知所措,他問我:“老虎說什么?”
“它說,”我翻譯道,“一個普通的學生加上一個不普通的市長,這下價值夠了吧?”
“我想是夠了。”市長說,“不過為了保險,最好再加上總統大人。因為動物園里有一些國家一級保護動物,我還達不到‘國家一級’,只有總統——”
瑪烏要我向市長打聽總統家的地址。
啟明星還未從天空消失之前,瑪烏又將總統請進森林。
清晨,我們收聽到內閣緊急會議作出的關于釋放動物園所有動物的決定。
七
人質的交換進行完畢。
我回過頭來,對著大森林動情地用虎語長嘯三聲。
“這是什么意思?”市長猜測說,“也許是表示對恐怖行動的痛恨?”
我搖搖頭。
“這是對自由的歡呼。”總統判斷道。
我更激烈地否認。
“那么,到底——?究竟——?”
“沒法翻譯。”我說。